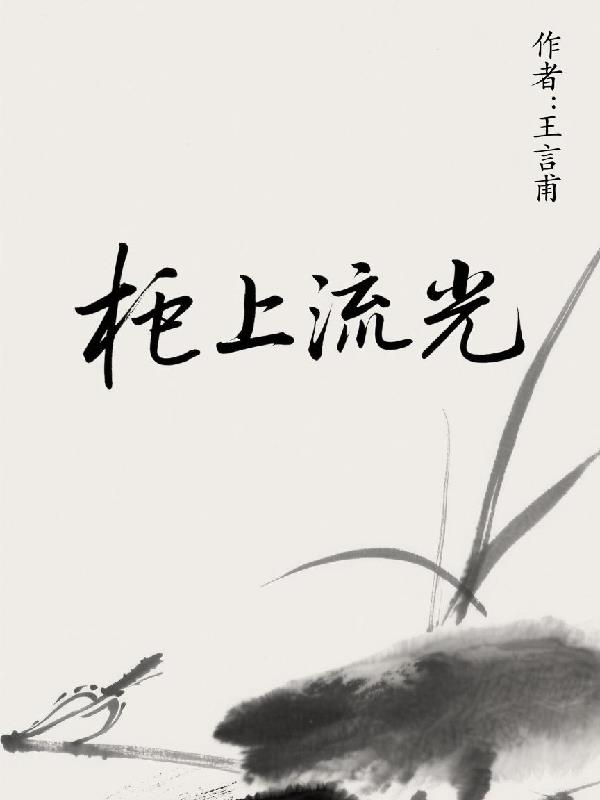第1章 风雪夜机声
1963年冬,凛冽的北风裹挟着雪沫子,如钢针般扎在国营红旗纺织厂斑驳的砖墙上。车间外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,而梳棉机旁的杂物间里,沈知夏蜷缩在散发着霉味的草堆上,额角传来的刺痛让她几乎窒息。
意识逐渐清晰,陌生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。原主是留美归国工程师沈明远的女儿,因父亲的"右派"身份,十六岁的她成了红卫兵批斗的对象。
就在刚才,她因私藏一本《纺织工艺学》被发现,惨遭推搡,头部重重撞在铁架上。
"嘶——"沈知夏倒抽一口冷气,指尖触到黏腻的血迹。恍惚间,她摸到口袋里一个硬物,掏出来竟是用油布裹着的线装书。
泛黄的扉页上,"天工开物·乃服卷"几个字映入眼帘,而落款处的"沈明远"三个字,让她心头一颤——这与她在现代实验室修复的明代织锦残片上的字迹,竟如出一辙。
就在这时,"吱呀"一声,木窗被推开条缝。一个戴着蓝色工帽的身影敏捷地翻了进来,怀里还抱着半块冻硬的玉米面窝头。
那人反手将窗户掩好,借着昏暗的光线看清屋内情形,低声道:"红卫兵刚走,先垫垫肚子。"
沈知夏警惕地向后缩了缩,却在看清对方面容时愣住了。青年约莫二十出头,眉眼清朗,工装袖口磨出细密的毛边,胸前别着的工作牌上写着"林砚舟 三车间"。
他蹲下身,借机器运转的轰鸣声压低声音:"听说你爹是搞纺织的?这台梳棉机总卡棉,厂里没人敢修......"
沈知夏的目光落在对方掌心的厚茧上,那层层叠叠的纹路,让她想起现代实验室里那台汉代素纱襌衣复制机——同样是岁月与技艺留下的印记。她接过窝头,咬下一口,冻得发僵的牙齿几乎咬不动粗糙的面团。
"我试试。"她翻开怀中的《天工开物》,在煤油灯下仔细翻阅。泛黄的纸页间,古人关于纺织器械的记载与她记忆中的现代知识渐渐重叠。
她摸出藏在袖中的炭笔,在墙上画出改良齿轮的草图:"问题出在传动装置,需要加粗钢条,改变咬合角度。但得找些废钢条......"
林砚舟眼睛一亮,从工装口袋掏出半截粉笔:"我叫林砚舟,三车间的。图纸给我,明早还你。"他撕下衬衫一角,小心翼翼地将草图包好,塞进裤腰内侧。
窗外风雪呼啸,梳棉机的嗡鸣声与两人压低的交谈声交织,在这寒夜里织出第一缕希望的微光。
"你为什么帮我?"沈知夏突然问道,目光紧紧盯着对方。林砚舟顿了顿,望向窗外摇曳的雪影:"三年前,我爹也是因为修不好机器,被当成'破坏生产'批斗......"他的声音低沉下去,"技术不该被糟蹋。"
就在这时,远处传来脚步声。林砚舟立刻吹灭煤油灯,将沈知夏拉到角落的棉堆后。两人紧贴着墙面,沈知夏甚至能清晰感受到对方急促的呼吸。脚步声由远及近,在门口短暂停留后渐渐远去。
黑暗中,林砚舟低声道:"明天中午,我把钢条藏在三号废料堆。记得别让人看见。"他顿了顿,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团布条:"先把伤口包上,感染了就麻烦了。"
等林砚舟翻墙离开后,沈知夏借着透过窗缝的月光,仔细端详手中的布条。那是从一件旧衬衫上撕下的,边缘还带着细密的针脚,显然是有人精心缝补过的。她忽然想起林砚舟袖口的毛边,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温暖。
第二天清晨,沈知夏顶着寒风来到三号废料堆。在一堆生锈的铁管下,她摸到了用油布包裹的钢条,还有一张字条:"小心李国强,他盯着你。"落款是一个简单的"林"字。
回到杂物间,沈知夏开始对照图纸改造零件。她的双手很快被钢条划破,鲜血滴在冰冷的金属上,却浑然不觉。当第一缕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照进来时,改良后的梳棉机发出顺畅的运转声,不再卡顿。
就在这时,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沈知夏慌忙将《天工开物》塞进棉堆,整理好工装。门被猛地推开,车间主任李国强带着几个人闯了进来,目光在她身上扫来扫去:"听说你把机器修好了?"
沈知夏强作镇定:"是照着《毛选》里'自力更生'的精神,瞎琢磨的。"她指了指墙上贴着的领袖画像,"不信您问林砚舟,是他帮我找的材料。"
李国强冷哼一声,却也挑不出错处。等众人离开后,沈知夏靠在墙上,长舒一口气。她知道,在这个特殊的年代,每一次技术的突破都可能带来危险,但为了生存,更为了守护心中那团不灭的火种,她和林砚舟别无选择。
窗外,雪还在下。沈知夏握紧手中的钢条,暗暗发誓:无论前路多艰难,她都要织出属于自己的未来。而那个在寒夜里递来窝头的青年,或许会成为她最重要的伙伴。